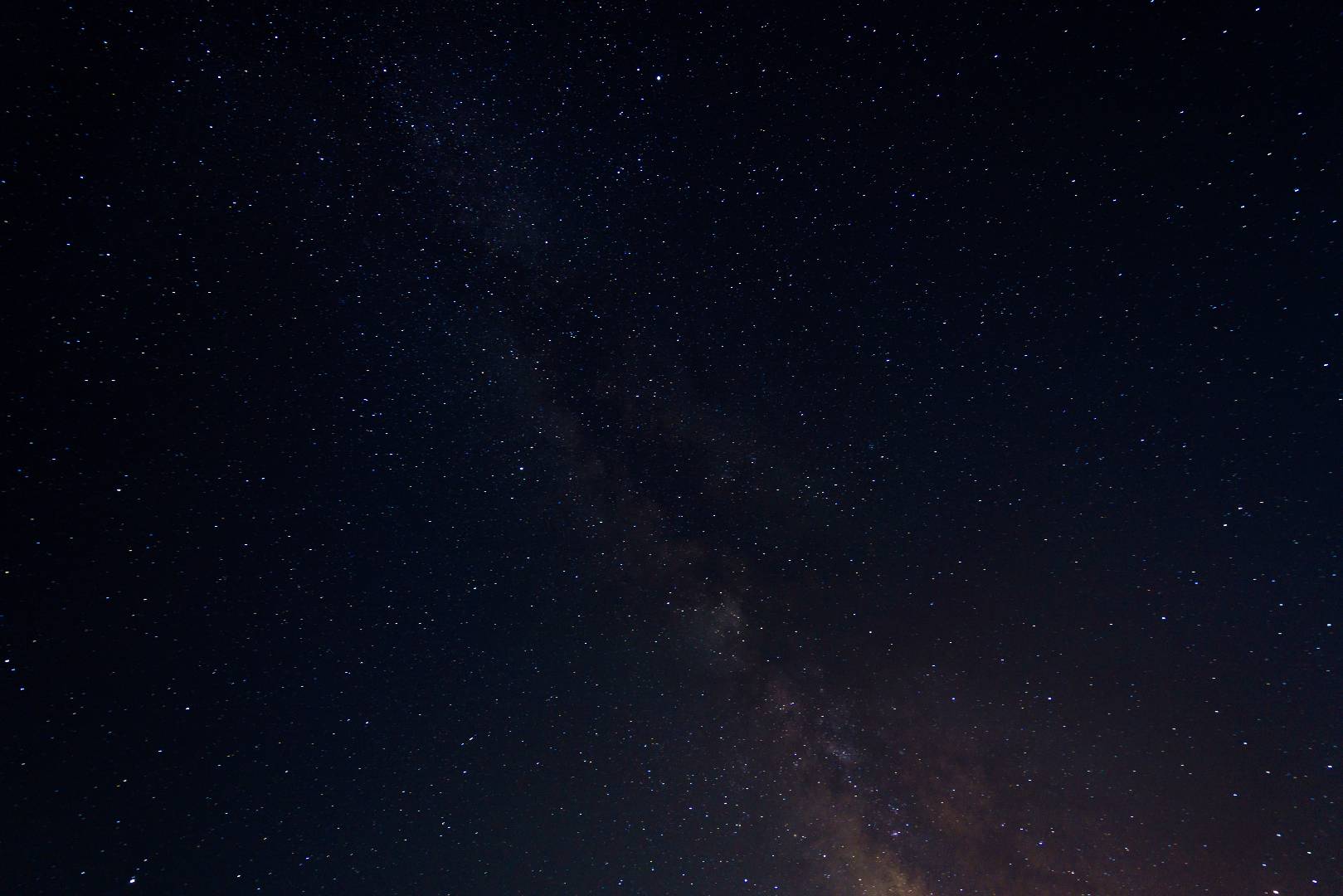江的尽头
(一)
嘉陵江旁柳树不少,尤其是滨江路下的小道。傍晚时分有不少吃完饭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手里摇着蒲扇,像一群自在的夏日虫鸣,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儿,在江风里混杂成一片温热的嘈杂。小孩经常来江边。有时,他会折下垂软的柳枝,笨拙地编成圆环戴在头上,嘴里念念有词,模仿着动画片里拥有奇特力量的角色,仿佛自己也戴上了魔法王冠。有时,他和同学铆足了劲儿,沿着江岸疯跑,手里扯着风筝线,线放啊放,放到头,却没系牢,只能眼睁睁看着那色彩斑斓的风筝,像一只挣脱束缚的鸟儿,越飞越远,变成天边一个小小的、遥远的符号。偶尔,小孩还会骑着妈妈的自行车蹬啊蹬啊蹬,小小的人影在车座上摇摇晃晃,一直骑到路的尽头,再大喘着气折返回来。
然而更多时候,小脚丫子会选择往更下面走。泥沙的江岸,夏天很宽,褪去的江水给小孩带来能轻轻松松游过去的错觉。他只是在想,身边的老人却是一下涌入水中,眨眼还真到了对岸。于是小孩去学了游泳。一个暑假,泳池里扑棱着扑棱着,至少学会了个蛙泳,他兴冲冲的找到爸妈说要去过江,换来的只有训斥,小孩不能游江。于是石门大桥成为了小孩过江最主要的选择。
石门大桥有点老,是上个世纪的建筑。桥很高。外婆说,舅舅视力不好,看下面游泳的人头就像蚂蚁一样。小孩视力更差,心里嘀咕着其实我连人头在哪儿都看不清。这边的桥都高,老师对小孩讲这里是桥都,有很多的桥。小孩没怎么去过别的城市,就算去过,也没多少其他地方的桥的印象,但是小孩走过主城区绝大多数的嘉陵江桥,桥代替了泳,他不用脱掉衣服游过去了。比起在岸边看江,桥上看江好像更奇妙。江向远方流去,汇入长江,奔向东海。小孩忽然觉得,游泳的人只是从此岸到对岸,看不到水的尽头。那些时间小孩老是做梦,梦到自己被卷入江流中,一路向东,最终被别人口中述说的海洋一浪又一浪的包裹起来。父母的唤醒好像是解救,但是催小孩快快吃饭然后去上学的话语像是另外一股水流,冲小孩到现实中的海洋里来。
不知道从何开始,江的两岸起了两个大大的圆柱。小孩和圆柱一起慢慢的长高,圆柱长出了各种各样的支架。初中前,家终于拆迁搬走,离开江边。闲得没事儿的时候,小孩还是会走到江岸,有时和朋友,有时一个人。走的路不再是石门大桥那边的滨江道,时不时漫步的桥也成为了双碑大桥。这条桥更长,跨越过嘉陵江的拐角。傍晚,更长的桥上,奔跑的车子比弯曲的江水更急,也更喧闹。小孩会在这座桥上跑步,播放着游戏的音乐,调高的音量和车的声音混在一起,最终化作汗水流出身体,被江风吹向其他地方。
(二)
那些在江边编织的梦想,也渐渐在我的心中萌芽生长,渴望着更广阔的天地。我开始关注新概念作文大赛,那些作品就像江水一样,不断冲击着我的思绪。思绪也会散,散的很远。那些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交替穿插在我的脑子里,有时候仿佛漫步梦行街,有时又会望着窗边的女人,或者低吟什么东西送给自己的贝阿特丽采……只有突然来的车鸣能唤醒我回到这座大桥上,让我看着我那晃晃橙色灯光下不断交错的影子。想去代入,想去成为书里的角色,去经历那些青年的故事,然后执笔写下漂亮的文字投稿被录取。然而没有,也不会有。只是去看了那些人看过的书,不断去回味他们写下的文字,然后想象着我有一天也能够去往上海,参加那么一场比赛,然后拿下或者写下让自己痛哭流涕的文字。幻想回来,不过是上课走神,或者一觉睡醒,老师无奈的眼光或者我抗拒起床的念头都压着我喘不过气来,所有的念头都拼命往我脑子里躲,把那些正常的用于学习的细胞挤到试卷上来。事实上这是对的,哪怕我当时也尝试拼命抵抗,懦弱的我也只能被夹在潮流中和其他人一起往前走。不是我,也不只是我在走,其实也有人在拼命推着我往前。记住我名字的,不断鼓励我的老师和同学,还有很少说话的家长好像抱着什么期待注视着我,逼迫我再次拿起笔——是写下答案的笔。这是痛苦的,整个高二我浑浑噩噩的度过,好的成绩在巨河对岸,还有心中的散文集、写书的笔或者是喜欢的人都在对岸,水流纵使不急,我却不愿意下河游泳。同班的那些人好像都有一些奇异能力,不论是分数或者是情感都能捕捉到自己的满意选择,他们嘻嘻哈哈团在一起,我好像更容易一人独行。心里想说的还是留给厚厚的本子,忙里偷闲写出来的文字好像更能戳中我的心。直到文字、书籍成为我的一种临时躲避学业压力的手段,“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了,才决定开始快乐”这一个小小的念头好像在心中开始萌芽。
(三)
大学,电脑与手机送我更加深入地走进互联网,也好像更容易获取的快乐。一方面,大学的压力确实算不上大,疫情笼罩下的网课仿佛回到高一下的摸鱼日子,躺在寝室开着电脑伴着认不得的声音呼呼入睡。整个大一都是挥霍,游戏、旅游、运动……丰富的生活,又或者说是崭新的生活不断激发我的创作欲望,所以我写,努力的去写,写满了我的大一。享受的理由是没有压力,疾病、学业在大二袭来一下子让人难以呼吸,成绩与论文化作了麻绳勒住我的脖子,创作的欲望很显然淡了,淡了。不是不想写,互联网与游戏的快乐比写作的快乐更容易获得。写作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与高度专注的精力去构思,然后不断修改,在那些对自己文字充满厌恶的感觉中慢慢修改,而我只会写一些类似散文的东西,删除,重写,再删除。我最害怕自我感动,把自己催眠然后安慰自己没什么,回头一看现实中的自我什么都没拥有,这太折磨我了。越是意识到这一点,越是感到害怕,越是难以写作。
但是心中还有其他的话想说出口,但是哪里有值得说的对象呢?
因此,我开始了另外一项记录方式,那就是视频创作。第一次是大二的雪,我第一次打开Pr把我那些杂杂碎碎的视频拼接一起;第二次是青岛的旅游,我把心中真正的大海缝合出来。我觉得这也算是全新的探索。可是这更折磨,电脑与Pr的矛盾、Pr与我的矛盾、我与录制设备的矛盾都太多,我心中的画面和手机里的视频难以重合,这些好像比读自己的文章还折磨。但是视频让我有了新的动力,那就是让我出去走,不断的去看新的世界。回看大学以来,我居然走过西藏、山东、陕西、哈尔滨等等等等地方了。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试着联系相熟的当地网友,相约漫步街头巷尾,听他们讲述此地的烟火日常。不断去走,就可以发现更多,发现更广更蓝的海,发现更大更白的雪,在这个经过中找回了小时候的执念与妄想,填补十几年前内心空缺的满足。如果说以前是在抵抗,那么大学后的我是在弥补了。
(四)
那么,我又要抱着我儿时的遗憾出发了。长江的终点也是我儿时心中能够想到的最远地方,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声也算是一直环绕在心头。普速列车1461再一次载着我前往22年底路过的上海,我想着我可能会回忆以前的故事,可是没有,我只是看着窗外的风景,看一会儿又低下头来玩手机。我可能是怕,怕我一直想给新概念投的稿到最后还是卡在了笔尖上,那一刻早就叛变了我儿时创作的梦想。其实早就放弃了,合上笔盖看着萌芽的时候其实早就断了投稿的念想,然后任由自己去白日梦,梦自己站在决赛现场是什么样子。高考填报专业的时候已经放弃文学了,只是留了几个新闻学和传播类放在最后面给自己一点欺骗自己的希望。但是就算这样,我还是想去看看那个支撑我整个高中的文学来源。所以,四月29日,我的21岁的第一天的凌晨六点半,我走下了火车,踏入了上海。
第一件事儿,无可置疑是长江入海口。长江奔流至此,江面豁然开朗,浑浊的江水裹挟着上游的故事,一头撞进青灰的海水里。江岸线是硬朗的,滩涂换做了防汛墙,水泥堤坝按压着浪潮。几个老人在堤坝的缝隙间放下钓竿,眼神专注地盯着浑浊的江水,仿佛在垂钓流逝的岁月。孩子那些游过对岸的想法,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里也可能没有一个孩子会梦想着游到对岸去,船或者桥已经是最简单的或者是更便捷的解决方式。江里面游着的只有船只,逆流而上着一艘比一艘还大的船,一艘一艘的船印着国贸课程上看过的logo向着内陆呜呜游进去,他们与装着巨大的集装箱向着更广阔的大海的货船擦肩而过。船只里面梦想可能很少了,更多的是工作与生活。这就是江的尽头吧,入海口也不是一个适合悠闲夏日游泳的地方了。
离开江边,又不自觉走上巨鹿路。参天而立的法国梧桐,枝叶在空中交织成一片绿色的华盖,阳光透过斑驳的缝隙洒下一片片跳动的光斑。我站在马路对岸就这么望着作协铁门,《萌芽》和《收获》在门的左边的墙上挂着。无法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来到这里,只能借着旅游的方式过来看看我最简单的梦的源头,作为我今年生日的最好礼物。门的右边有个书店,窗玻璃上挂着最新一期的《萌芽》,书店没开门,我也好久没买萌芽了。
上海,我总是忍不住说是这座城市是我儿时梦想的终点,我无数幻想的终点都是这座城市,不论是江流,还是文学都汇集此处,而我来到这里只能说是路过。旅游过这里,不应该只是去带着怀念的探寻,也需要带着期待的去重逢。和霜霜的再见面,和其他网友的相聚,可能也在暗示我些什么新东西。行走在上海街头,与旧友新识的交谈,江风海韵的涤荡,都像在无声地提示:人生的流向,或许该有新的汇入点了。可是面对未知,我还是在彷徨,我还是在犹豫,但是不论如何真的该再出发了。
(五)
送我离开上海的是东航MU8219,很快,我在天上往下面看,一会儿一座城市。以后可能还会来上海,可能再也不会来了。不过我还是觉得会来的,也许是因为约定,也许是因为新的故事会再来这里描绘描绘。两个小时的飞行中,忽然就想,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许未来会放弃现在的执念,然后重返天津或是北京再做一次道别吗?行文至此处,忍不住想我将这段旅程心思再度整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交给未来的自己来嘲笑现在的模样吗?也许在未来,很久很久之后的未来,可能也没了什么羞耻,可能也只剩下一些怀念加持来再看看,1461要开的十八九个小时,在MU8219中无非两个小时的罢了。以后回头看现在,很漫长的路不过一瞬间就过去了。有一天我回到属于我的长江与嘉陵江边,给那些小脚丫子踩过的泥土说说长江的尽头其实也没什么,那边早就没了适合你们呆着的岸边,那些寻找尽头的路,那些在桥上奔跑时耳边呼啸的风,那些记录下的雪与海,它们最终只会是江水最终沉淀下的河床。很多故事的尽头,也可能只剩下巨鹿路街边那株老梧桐,和其他树望着静静地守着一整天的故事,偶尔念念以前写过的文章,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说。